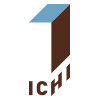-
周傳雄vs電音 打造新音樂形象2012 / 12 / 12情歌教父周傳雄暢談新專輯《打擾愛情》,其中不少歌曲是出自自身的愛情故事,號稱是最貼近真實自己的創作專輯。其中還有另一突破,周傳雄為了尋找更多新音樂上的靈感,以全新的音樂形象打造,除了以過來人角度詮釋愛情,甚至有別以往加入電音等年輕元素,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周式情歌。
-
我寫寂寞,如農夫守望他的田 - 周傳雄2012 / 11 / 30這唯獨對我無聲的世界
在整理周傳雄採訪筆記時,腦海裡一直迴盪著〈Across The Universe〉的歌詞:「沒有事可以改變我的世界。」他在訪問中約3次以上,以自嘲卻認真的口吻說到自己有亞斯柏格症(一種泛自閉症障礙)。這病症患者專注力很強,從童年到現在, 他或許曾被成績綁架,或許曾有名氣焦慮,但都像「龜兔賽跑」裡的龜,這世界急轉時,他不急不徐,沒停腳過,於是這世界與他是泛泛之交,他卻從這世界的過動行徑中熟悉蒼老, 相對他規律中的年輕,人們為了怕老,搶先越界進入了虛無。他看到了就只能寫下來,「我喜歡觀察人性。」於是寫不完也寫不停,不寫這世界彷彿就在眼前冷黑了。不寂寞沒有音樂
於是無解,所以少年時代的他開始做歌,因為太習慣寂寞。「或許因為我有自閉的關係,我不怕寂寞,同時我可以看得清楚寂寞,創作、面對銷售、當製作人面對發片前的翻牌,都是我一個人,這個行業很熱鬧,但說穿了就是個徹底自己獨處的行業。」寂寞小孩將音樂視為終生伴侶,「我記得從小跟父母聽鳳飛飛與劉家昌,小時候親友聚會,就會叫我出來唱歌娛樂客人,我從小學二年級,就確定歌唱志向。」他說他幸運,童年參加主日學要唱聖歌,二年級就被老師選中參加比賽,國中打工時又學了打鼓。」似乎一切都好?「在我青少年時,父母親離異,沒人盯我升學的事情,可以很專心地學音樂。」什麼東西不對勁?在他眼鏡鏡片下面,「那時候沒覺得,大多時候我很平靜,父母離異時,也沒人覺得我有什麼情緒,我自己處理。」這麼早認識寂寞,你有天甚至會大量需要它,他知道。夢想就是要給人狠狠踩過
他說:「我是個很敏感的人,童年時很愛哭, 情緒開關刻度比較大,開起來了就哭到止不住,聊得很開心,我就開始亂講話,相反沒開時,很沉很安靜。」沒人知道那是怎麼回事,如果你沒跟別人說,世界有時是絕對跟你無關地在運轉著,日子也就相安無事,「我寫歌比較濃烈,製作時比較澎湃,因我私下無法展現我的張狂。」必須寫下來,他只有一個念頭,一個人感受如果多如雪或風絮, 又不能跟別人分享,就必須創作,而且要勤快地,有紀律地寫,免得某天雪淹沒道路, 淹沒了一切。因為是必須,他忍受過有些作品難免被當罐頭,但還願意繼續下筆,追求下首歌。他認為,只有作品被踩踏過後,你才能稍稍初識理想這回事。你有多熱情,你就有多自律
他說:「我剛從歌手小剛轉型成自由創作者時,是2000年的時候吧,我大概有一年沒有工作,那時快餓死了。」他口氣平常,自比是農夫,大旱早晚總要來的。之後雖然等到案子,卻日以繼夜,大量磨損了他的精神意志,「那時一天開三個班,同時做歌、混音、製作,也沒考慮到體力,於是就會做出些讓自己遺憾的作品,我開始必須去調整, 想要長久做下去,作息一定要改變,我現在下午錄音,晚飯時就收工,不熬夜的,我不去管這世界的節奏,要維持自己的節奏,就像跑馬拉松跑者,一下衝太快,會沒力的。」為了工作,他開始保養自己的身體。「我很自律,除了宣傳期,固定早上8點起來運動,近午開始寫東西,晚上就休息,每天都要有固定產值,熱情要靠習慣維持。」他仍愛自嘲:「小剛時期結束後,我才知創作的真諦,我剛當創作人時,心想:『你高興了吧!』結果創作人的生活是這樣的,通常明天要開會,下午唱片公司才打給你說他還沒歌,那時我剛轉行,當然要答應。也曾有過人有把首韓國歌拿來給你,說談到版權了, 當你做好了,也錄完了,對方跟你說版權沒下來,經歷了那些,你的心若還沒死,這件事對你的意義就大到不能割捨了。」歌手只有一條路,背著懸崖跳下去
這幾年,他當兩岸製作人與經紀人,一首《黃昏》征服了對岸,他寫寂寞有獨到之處, 他看演藝圈是熱心腸在冷裡燒,跟他的情歌一樣,安靜的毀天滅地,他說:「這行業是考驗人心的行業,是名利場,你要當歌手, 你要做準備我們都是背著懸崖跳下去,還沒想清楚,轉眼間人就在下面,能做的只有靜下心來,不要覺得那些名利真的是你的,名氣來去都跟你無關,只能把你本分做好,現在好像滿地有機會,但你如果很焦慮這也想沾那也要試,沒時間專心學好一樣技藝,機會就變成垃圾,你到底想做什麼,可以做什麼,要想清楚這點。」台灣音樂市場不好,他仍然發片,這次放膽混融了Eurobeat,為所有不受祝福的愛情發聲,他講得實際:「我們以前聽首歌,是聽心流,讓你靜下來體會深刻,現在不同,就是視聽的時代,比的是財力,等到錢這招不管用,音樂才會回來。」持續想寫歌是因為:「看到有人跟當年的我一樣,想要勸勸。孤單的必然,也許你看不清楚,那我就幫你寫下來。」知道多冷,所以他鏡片下的笑容恆溫式的溫暖,我年長之後才知道,笑容暖的人心中都有一片人煙罕至的曠野,畢竟誰會在陽光下空燒柴火呢?周傳雄,或許是亞斯伯格症患者,但愛這件事,他是燒了自己來的。 -
周傳雄小試身手玩電音2012 / 11 / 18周傳雄推出新專輯《打擾愛情》,曲風加入輕電音,擺脫招牌抒情路線,令人為之驚豔。他先是謙稱: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怕我難過,所以都騙我好聽。」後來卻又忍不住得意洋洋地透露,想換風格已醞釀很久,「我是穿破牛仔褲、唱重金屬搖滾出身的,私下超愛電音,這次只是小試身手而已。」此話一出,跌破大家眼鏡。周傳雄認定自己有雙重個性,並將其歸咎於雙子座天性。他對星座、紫微斗數頗有研究,自曝每年穿著會參考紫微預言而改變,「像是今年建議多穿亮色,我已經開始物色衣服了。」這次拍攝台灣新品牌FN.ICE男裝,他也一改藍、白、黑的過往喜好,嘗試穿上多彩格紋、草綠色等。該牌強調機能時尚,提供不少高保暖性的服飾,讓周傳雄穿了頻冒汗。他透露,自己很怕熱,平日冬天襯衫加牛仔褲就搞定,「唯一一次我真的感覺到冷,是零下30度。」
-
周傳雄眼鏡控 花50萬珍藏40副2012 / 11 / 16周傳雄出道25年,儘管音樂曲風多變,帶著眼鏡的斯文形象卻始終深植人心;出門必唸三大口訣:「化妝品、身分證和眼鏡」護形象。他眼鏡戴出心得意外成為達人,拆卸鏡片僅需一秒鐘,斥資50萬收藏近40副眼鏡,他自信說:「我一到眼鏡行,就可以知道哪些眼鏡適合我。」為作弊度數配深 偷看答案眼花周傳雄秀出國小戴的眼鏡,因近期「復古風」完全不顯俗味,他說:「小時候戴眼鏡,為了作弊,度數刻意配深,結果偷看幾題就眼花了,度數也越來越深,得不償失。」甫出道時,資深攝影師陳文彬見他長相斯文,建議他戴眼鏡,沒想到從此被定型。戴眼鏡被定型 治裝先挑眼鏡周傳雄唱片宣傳治裝先挑眼鏡,演唱會換眼鏡和換裝一樣勤,2004年新加坡商演後台曾遇小偷,眼鏡全被偷光,只好請助理趕快去外頭掃貨;周傳雄稱不戴眼鏡粉絲認不得,連藝人也看嘸,曾在機場巧遇王力宏與李宗盛,熱烈打招呼卻換絕情,他說:「過了很久才被認出,他們一直覺得我眼熟卻又認不得,他們當下窘樣真是太有趣了。」
-
周傳雄×史丹利 的「Man′s Love」2012 / 11 / 13面對曖昧的他或是現正熱戀中的另一半,妳心中是否充滿著許多疑慮?偏偏姊妹淘們都是女孩,即使是擁有再多感情戰績的姊妹,也無法替妳揣測出他的想法?來聽聽周傳雄與史丹利細說屬於男人的「Man′s Love」,或許下一步妳對男人將有了新了解。印 象中的小剛老師,充滿細膩的男性魅力,如同他多首膾炙人口的作品般,溫柔卻不膩。史丹利,幽默風趣的網路名人作家,任何辛辣兩性話題絕對來者不拒,敢言又 直接。這兩位性格迥異的男人,在面對感情話題時,究竟能激盪出多少火花?形象上的迥異,是否讓他們的愛情觀也有著極大差距?或外在只是他們的保護色?其實 他們對於愛情有著相同的頻率?隨著科技與社群網站在生活上的蔓延,為現世代愛情中的人們產生了微妙變化,周傳雄:「當另一半所觸及範圍越來越多,妳也會顯得越來越不安!」,所以他在新專輯【打擾愛情】中化身傾聽者,希望困在愛裡頭的男女,別再自尋煩惱,讓愛情回到本質。
-
周傳雄解析愛的本質 完美不如適合2012 / 11 / 08周傳雄(小剛)出道25年,創作許多膾炙人口的動人情歌,隨著經驗積累對『愛』的本質有新見解,他說:「愛的本質是付出,兩個體結為一個,共同追尋夢想,你不能實現的,對方可以為你實現。」小時候喜歡完美的人,長大才知道完美不見得適合自己。周傳雄推出新專輯《打擾愛情》,曲風加入輕電音,少了像《黃昏》耐人尋味的鋪陳,改以單刀直入詮釋情歌,「輕鬆、豁達,沒有醞釀很久」。改變來自日積月累的人生閱歷,對處事、感情變得更豁達,不再雞毛蒜皮的小事裡鑽牛角尖。他『情歌教父』封號實至名歸,對愛有精闢見解。娓娓道來,年輕時總喜歡心中的那個完美情人,經過風風雨雨後才知道,「完美伴侶並不適合自己,好東西來到你 這裡,有可能是加分,也可能是減分」。愛的真諦是生命共同體,兩人彼此有加分作用,能為夢想努力,即是自己做不到,也能幫助對方完成。在他心中愛的本質是 付出,絕不是佔有。此外,談到當年曾被邀請加入小虎隊的話題,他自嘲:「跟人家比帥也不行,比跳舞也不行」,二話不說自砍唱跳歌手一路,堅持走自己的情歌創作之路,誠實說:「當然看到他們紅的時候,會有一點點羨慕」,但一路走來沒有後悔。
NEWS
2018 / 08 / 11
房思瑜中空運動裝 拉許光漢、章廣辰陪蹲
記者裴璐/台北報導演員房思瑜舉辦新書簽名會,首本著作《房式深蹲》書籍上市旋即攻佔各大排行榜,在一周內累計再版四刷破萬本,躋身暢銷作家行列。...
2018 / 06 / 07
「台版小松菜奈」體驗變性當男人 許光漢床戰第一次就上手
〔記者粘湘婉/台北報導〕姚愛寗、許光漢、林意箴主演緯來電影台全新自製電影《海吉拉》描述跨性別愛情,姚愛寗空靈氣質有「台版小松菜奈」封號,她...
2018 / 06 / 07
專訪/我也想變好人!許光漢《1006》大魔王勾內心黑暗面
記者林奕如/專訪許光漢在《1006的房客》飾演李國毅好友兼律師助理「周大軍」,可愛又善良的笑容,讓人卸下心防,但隨著後面劇情進展,揭曉他就...
2018 / 05 / 18
竟是大魔王!許光漢黑化粉絲崩潰
許光漢因在植劇場《戀愛沙塵暴》、《姜老師,妳談過戀愛嗎》迥然不同又出色的演技備受矚目,到了歐銻銻娛樂自製劇《1006的房客》也是關鍵角色,...
2018 / 05 / 11
萬寶龍小王子特展 許光漢捧場
聯合報 記者孫曼/台北報導許光漢帶逛萬寶龍小王子特展。 記者林俊良/攝影 萬寶龍(Montblanc)為慶祝暢銷全球的法國名作《小王子》(L...
2018 / 04 / 18
從每個角色中照見自己,許光漢:「演戲就是一種孤軍奮戰。」
「演戲就是一種孤軍奮戰。」從《戀愛沙塵暴》的花心學長莊浩洋,到《姜老師,你談過戀愛嗎》性成癮的遲緩兒陳威政,近期在《1006的房客》中飾演...